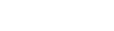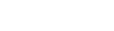事有凑巧,从福建师范到永安师范同事8年的吴秋山先生,一别33年多,没有再见过面,也没有通过讯,忽从漳州来信说他虽然已经退休,却仍在教书,并著作,兼编杂志《水仙花》,叫我写点稿子去凑热闹,而且邮赠给了我两颗圆圆的水仙花的块根。我为他老而益壮的精神所感动,为着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,“老人犹有壮年志”,以为我辈文化工作者固当如此,该有所以应命,勉强草就了篇《水仙花》寄去。稿未发表,就有好些同学,也多半是久不通讯了的,也要我写些稿子去凑所编刊物的热闹。40年前的青年学生,现在有的已经做了外婆,有的已被叫作爷爷,许多已在大专院校任教,而且编辑文艺刊物,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,这是很可喜的。这样突然接到许多同学的来信,使我欣慰;同时,却也使我感到为难。我已82足岁,患严重的老年性白内障和视神经衰退,左眼瞎了3年,夏间开刀,亮了,但还没有配好眼镜,看不清楚,仍然靠只有0.1视力的右眼。而且几年来,友好们由劝勉而督促我集中精力,专写鲁迅先生在北京时期的回忆录,因为了解些他当时情况的人即将死光。这是我所义不容辞的。我为《水仙花》杂志决定写《水仙花》以前,考虑再三,当初以为这和鲁迅先生无关。但一回想到我初到福州乌石山的情形,杨骚与郁达夫同在省府公报室里做事,杨是漳州人,同我谈起过漳州特产的水仙花。他和鲁迅先生有着双重的关系,间接的关系还是发生在鲁迅先生还在北京的时候,这就使我动笔写了《水仙花》,虽然终于不能够详细写清楚。
最近永安县文化局也来信叫我写稿子,说是我在永安八年半,在那里度过抗日战争时期,应该写点回忆录。这自然也是我应该做的。但我对于有些应该做的事已经力不从心,这又使我感到为难。仔细一想,却也决定写稿应命了。我觉得写这种回忆录,不但于鲁迅先生不无关系,而且实在是很有关系的。首先,我被反动派关在杭州的军人监狱里,如果没有鲁迅先生的营救,在“宁可错杀一百(千),不可错放一个”的反动口号下,我难免“寿终牢寝”,那就根本不能到福建。在由福建师范到永安师范的整整9年中,历经5个校长:姜、黄和三王。我和同事们、同学们和大湖的邻居们相处“乐欢然”,私自以为多方面地受了鲁迅先生影响的结果。本文标题,是由福州内迁永安,停留在南平的船上时想到的。1931年“九·一八”开始,日本军阀从东北武装侵略我国,蒋帮反动政府只知反共,采取不抵抗政策,次年发生沪战,演成了“一·二八”惨案。到1938年“八·一三”,侵略军向我国沿海各省全面进犯;我乘坐过的一只三北公司的轮船已被炸沉在闽江口,作为封锁的障碍物。福建省政府决定内迁到永安,福建师范的师生员工做先遣队。这是省内唯一高中程度的师范学校,雇了许多条船,逆水而上到南平,才知道去永安要先到沙县,山高路陡,相当远,在福州生活习惯了的人难以步行到达。人多,调集的几辆汽车远远不够,只好分作多批运输,大批的人在船上等候。那时候,由于山高路陡,而且路面高高低低,很不平稳,车子颠簸得厉害,连体育科的女同学,颜面晒得黑紫紫的,一个个地也都呕吐了。有些年轻的同学听了这消息就面现惧色,却也有些同学是这样说的:“这样崇山峻岭的地方,即使福州沦陷,日本侵略军也是不敢进来的罢!”
“即使敢来犯,”教官一脚踏着装着枪弹的木箱说,“我们也用不着害怕,我们带着许多枪杆来,这不是子弹箱么?”“且不说日本侵略军敢不敢进来了,”一位熟悉闽西、闽北情况的职员插嘴,“永安,为什么叫永安的呢?原来这地方是很不平安的。在苛政猛于虎的年头,绿林中就出好汉,自然并非个个都是真正的好汉。总之民不聊生,社会上就不得安宁。大家希望安定,希望永远安定,这才定名为永安县的。又有枪杆又有子弹,有备无患总是好的。”“所以我们一定要带枪杆来,”教官郑重地说,“我们总得自卫!”熟悉闽西闽北情况的职员又说:“如果抗战的时间延长,恐怕大家还得拿锄头杆呢。永安多山地,种油茶油桐以外,粮食以地瓜(番薯)为主,稻谷是很少的,因为水田不多。”
我教语文,是拿笔杆的,但我也扛过枪杆。“九·一八”以后我还在杭州高级中学教书,为着准备抗战,全校师生员工每天黎明就上操场,教职员工和女生编成特别的混合连,由五个教官进行全校的军事训练。其实,我早在第五师范读书的时候,为要洗去“东亚病夫”的耻辱,在特聘拳师教国术以外,枪操也算是重要的一科。拿枪杆我并不感到困难。只是锄头杆,我当时毫无经验。幼时我跟父亲种花,用以掘土的只是一只手拿的小锄头,是说不上垦荒掘地的。可是到了永安,这一点还不即成问题,首先感到困难的是语言不通。要靠中年级以上的小学生做翻译员。当时永安还不容易找到中学生,由于教师认真训练普通话,中年级以上的小学生却大概能讲普通话,也还容易找到,买东西,问路,就都靠他们做翻译员。据说福建的永安和浙江的天台,四川的荣县,由于交通不便的关系,都保存着许多古代的语言。这三个地方我都到过。在荣县买吃了用茉莉花做成的糕点,并没有请人做翻译员,大概因为已在临海教了半年书,游天台山一个星期,也没有感到语言隔膜的困难。初到永安,却实在感到了语言不通的困难的。锅子还叫做“鼎”,真是古色古香的。其实,语言倒是也有一定规律的,像“知道”叫做“打帝”,前面加个“安”的培头词,“安打帝”就成了“不知道”的意思。当初我为问路和买东西,不知道听到了多少个“安打帝”。因为这样说的时候总是摇摇头的,我才知道因为听不懂我的话而说不知道的。又如说“不要”,叫着“安打”,“要”是“打”。有一次,我送糕饼给一个小孩子吃,他接连大声喊“打!打!打!”显得很高兴,远远他就伸着手来接糕饼。我一时莫名其妙,我请他吃糕饼是好意,为什么他要大喊“打”,而又高兴地伸手来接糕饼?原来永安“要”就是“得”,“得”的发音就是“打”。这后来才了解的事情,这里且不多说。
福建师范师生的人数多,突然内迁到永安城里,新造校舍来不及,只有文庙(孔庙)可以安排一部分人,采取特殊的措施,就是让二、三年级的学生分散到省内各个乡村去做民众工作,宣传抗日救亡。年轻的教师跟着去。留在校本部的一年级学生也组织“晨呼队”,黎明即起,列队唱着歌曲,街头巷尾都走转,促使居民早点起来工作。永安冬季多雾,居民叫瘴气,原有习惯,总要睡到九十点才开门来晒太阳;反正俭朴的生活无须多劳动。溪水流急,连舂米都有水碓可以利用,只要把糙米倒在石臼里,开动水碓,过些时候拿起来,就变成了白米了。留在校本部的一年级学生在做宣传工作中,也劝居民冬季种麦子。高山多旱田,不好多种水稻,种麦子是可以的。以前的永安,地瓜掘起以后,田间空空的,从此冬季,也就可以见到绿莹莹的麦苗了。
过了几个月,消息传来,说是散开在各乡村的二、三年级普通师范生,民众工作做得比较好,一般高中学生,也是二、三年级的,成绩比较差,不但宣传工作展不大开,甚至自己要煮饭吃的米都不容易买到。因为在校学习的功课,以数理化为主,不像师范生学了些社会科学,懂得群众的心理,搞好了关系,受到了欢迎,买米煮饭吃这类事,自然不成问题了。
文庙的房间并不多。大殿权作礼堂,东西厢房做教室,一些偏屋做师生宿舍。除非晚上和雨天,才在教室里上课、自修,晴天,吃了早餐就列队到树林里去,值日生拿着小黑板,教师左臂挟着讲义夹,右手拿着教鞭跟在后面走,粉笔盒子是放在衣袋里的。因陋就简,凡事将就。教学却都很认真,为着救亡,意志坚定,精神是一点都不敢松懈的。到了树林里,把小黑板挂起在高大的松树干上,学生席地而坐,“鸟鸣山更幽”,松涛呼呼,大自然的教室显得格外清静;教师清晰地讲解,学生倾耳静听。
万恶的日本军阀蓄意破坏我国的文化机关。一天,一小队敌机来袭击,文庙——我们的校舍连中七个炸弹。当时我没有课,警报一响,就带着一妻两子跑出城去。警报紧急地响了,幼小的云儿就跑到小土地庙的墙脚边去卧倒,他的阿哥庚儿一看到,连忙过去伏在他的背上,表示他是爱护兄弟的。接着妻也去掩护他们。敌机在空中打圈子,蓬蓬的炸弹爆发声以外,只有嗡嗡的飞机声和嘘嘘的敌机射出来的流弹声。我听着,也就不自主地赶去掩护;四个人叠成一堆,如果中了炸弹,那就一家同归于尽。其实敌机的机关枪弹很长,我的背上并没有铁甲,一弹射到底,也不免是同归于尽的。我觉得背脊上面在发痒。敌机吹着喇叭逃去了,永安城外的山上听说有几尊高射炮,可是不起作用。回到寓所,打开房门一看,大吃一惊:民房没有天花板,本是暗沉沉的室内,已经明亮和在室外一样了——因为靠近文庙屋顶已被震得片瓦无存。校舍既中七弹,再也无法停留。校中当夜紧急会议,决定第二天就迁校到城外大湖去。虽然只有20里,是山路,既不能行船,也还没有通车,幼小的云儿还不能自己走这样的山路。生长在水乡的我,只能在比较平坦路面上抱着孩子走,上坡过岭,就得靠生长在山村的妻了。但都走得油汗满脸。简单的行李,四个人的用品,靠好友董秋芳代请在做书箱的木匠暂时停工给我们挑着一道走。当天在破祠堂屋里过夜,我感到火钳用处的巨大,可以把肮脏的什物钳出去,又可以夹住报纸团当作扫帚用,这样,才得集体睡地面。
当初以为到了农村,买米买青菜就都不成问题,还可以请位女工来帮忙。我上街一转,才知道这三点原都是妄想——街上并没有一家米店,也没有一个菜摊。说是农家各自种田,主要是山田,粮食和蔬菜都自给,以地瓜为主粮。妇女是即使穷困,也宁可在家饿死,决不外出做工的。地瓜是一户人家有几口人就种几千株的。地瓜收获以后,大的刨成丝晒干,以备一年之用;小的单煮做点心。永安出产一种红米,质量不错,只要在半天以前浸米,拌点地瓜丝做成饭是很可口的,只是产量不大。福建师范刚搬到永安时买米还不算困难,做了临时省会以后,省级机关陆续迁来,人口突然大量增加,买米就很成问题。我们搬到大湖以后,为着要买米,大家出动,两个女同学被挤落到溪水里。几次由教官带队到20来里外的河边去背米。米本该由管理粮食的机关供应,但来源太少,不能按时拨给,就打听得哪里有运米的船只经过,就赶到那里去背米。这并不能算作拦劫,却也含点这样的性质。但这只是偶然打听到了消息才可以这样办的。学生多,张着嘴巴天天要吃饭。经济又很困难,不能自己从远处去运得粮米,只好从节约口粮着想。口粮一减再减,终于每人每天只吃4两米,蒸在毛竹筒里,多放水,其实是粥,也不过小半筒。配饭的只是一小撮黄豆,不过20来颗。常言道:宁可全饥,不可半饱。我们的许多同学,都是这样熬过来的。正当青年时期,好活动,体力的消耗量大,同时要长大起来,应该是多吃些食物的,由于日本军阀侵略造成的灾难,却反而少吃食物。李世山同学一句话,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:那天为着拔牙齿等事,我一家人都到永安城里去,托他看家。回家后妻烧好饭请他一道吃。他说已经吃过晚饭。妻劝他再吃一点,他就端起装得满满的一碗饭,笑着说:“学生的肚子是吃得饱吆?”他是矮矮小小的,一餐不到二两米的饭吃得“老虎舔蝴蝶”,那么高大的人,不是更觉得不够吃的么?几年前有位同学顺道来看我,她已到了退休之年,却仍然是矮矮小小的,使我回想到了大湖挨饿的情形。可是同学们读书认真,生产劳动很起劲,宿舍里内务也做得很好,每周检查一次,我以级任导师参加过这工作。只见双层木板床,上下格被褥都叠得整整齐齐,蚊帐也挂得端端正正,洗涤得干干净净。有个邻省人的同学,她每次考试,一定交头卷,而且一定得到满分。她因家乡沦陷,这才流浪到大湖来求学,真是越加困难越加刻苦用功的。大湖的冬天,固然没有像闽南的暖和,也比闽东冷得多。因为是在高山上。我去查早自修,有时冷风刺骨,但她总是天一亮就到教室用功,穿着黄黄的夹大衣。那不屈不挠的求学精神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一个早已做了外婆的同学,有个小女儿,在永安的一个技术学校里读书,从闽东过去,吃不到海味,嫌清苦。做母亲的告诉了她抗日战争时期在大湖的生活状况,她就安心学习。由此可见,永安师范的同学们刻苦好学的精神,不但借以度过抗战时期的难关,也是可以作为后来青年学习的典范的罢。
为着改善同学们的生活,后来学校里开辟农场,聘请集美农校毕业的杨先生做指导员。首先是垦荒。我以级任导师的关系,跟同学们一道掘地,这就实行拿着锄头参加集体生产,各人开垦一畦,身强力壮的开垦大畦,瘦小的开垦小畦,各听自便,并无争执,我开垦了中畦——因为掘地以外还有照料各个同学的任务。为着多吃,大家嘻嘻哈哈,并不觉得怎样困难。因此,不久以后,蒸饭的毛竹筒里就可以切上几片地瓜,配饭的也就有些炒菜头和青菜了。我们一家的蔬菜问题是早就解决了的,锄头杆也已经拿惯。我寓所的贴邻家是农家,屋旁种满着青菜。当初我去向他家买菜,他们给了我菜不收钱,说是拿去吃就是了,卖是不卖的。我送了些他家所缺少的日常用品,他家就自动按时送青菜来,也送给我们瓮菜(在瓮中腌成的芥菜)。我常代他家写信和算帐,他们又自动划出一畦地让我自己种菜,靠湖边,是便于灌水的。也给了我菜秧,先告诉我种植的方法:掘松泥土以后挖孔洞,施基肥,然后插上16株芥菜秧,再嵌上10株菜头秧。永安的芥菜高过我的半个人,剥一片叶子来,四口之家可以吃两餐。多施肥,轮批剥,16株芥菜是够一个冬季吃的。
暑假、寒假,同学们回家去了。我就照料各畦的作物,灌水施肥。后来同学们全班毕业,分配到各处学校去服务时,合计约有两亩新垦土地,全由我种植。从农场得到秧苗,添种了番茄、法国种的四季豆、花耶和黄秋葵等,既丰富了蔬菜,也有水果可吃了。我又大种地瓜,这可以补充粮食,抽出些米谷来养鸡、养鸭、养鹅和兔子。母鹅是在动物中做母亲最辛苦的一种罢,孵小鹅,要先用嘴夹把自己肚皮上的毛毛都拔去,使肚皮紧贴蛋壳,以便体温传过去。
太平洋战争发生,我想日本军阀可以偷袭美国的舰队,美国全面反击,恐非日本军阀所能抵御,战争不难迅速结束,我快可以回家了。可是旅费呢?一家四口,路远迢迢,这是不能从些微的薪水积储起来着想的。考虑再三,决定养猪。就和要好的邻居商量,他们满口赞成,并且自告奋勇,代我家从远处买得小猪挑回来,一定把猪相挑选得很好的,嘴巴是要团团的,能把饲料吃干净。猪身要长,脚要高。并且劝我同时买两只小猪,互相争食,容易长大,到养得60来斤的时候,饲料不够了,可以卖掉一只,减轻负担。我和妻的衣服穿破了,修修补补,仍然可以穿在身上。小孩子长大起来了,他们的衣服没有长大起来,而且也破了,连拼拼补补的布片也没有。卖掉一只中猪,救了这个急。以后我每年可以养大两只肉猪和两只半大的中猪,大的100多斤,半大的60多斤,生活安定点了。可是问题又产生。永安春季多雨水,有接连42天不停止的时候。但在冬季,干旱的时候多。大湖有七口井,我的寓所后面有一口,但一旱就吊不起水来。最深的一口在师校的厨房边,厨房原是依靠这口井建设的,但争取水的人很多,在那井边排着长队。我日间无法去吊水。我最后养大的一只猪有217斤半重,也只养得半年,比附近邻居养的都长大得快。有人说我得到了什么养猪的秘诀,所以猪长大得这样快。当初我自己也莫名其妙,检查以后才明白原因。每天晚餐后,我首先要备第二天的课,要改作文,要切猪菜,收获了大批地瓜以后要斩地瓜藤,以便第二天晒干准备长时间地喂猪,把不好喂猪的老地瓜藤拣出来喂兔子。还要每隔三五天舂十多斤大米。大湖溪边有水碓,可以去舂米,但要有人去料理。日间我离不开学校,晚上睡在那里就改不成作文和备课,还不如在家里舂便当。一般农家晚上早睡觉,大猪一天只喂三次。我总要过了半夜才就寝。可以多喂一次猪,饲料又浓而好,许多小地瓜都斩在猪菜里,这是事实,并不是什么秘诀。过了半夜我才上床睡觉,但在三四小时以后,五更以前,我就得起床赶到大厨房旁去汲水。如果错过机会,一家四口,第二天不但吃不成饭,也将无法止渴。在两三小时睡眠的恶梦中,也往往是提着吊桶汲水的。那种情形,现在只是想想,我也觉得是够吃力的。
要附带说明的是,笔用竹做成的,笔干的干似乎该加竹头;锄头用的是木干,似乎该加木旁;枪是鎗的本字,照鲁迅先生在北京时的习惯,凡俗字笔划比本字少的,用俗字。本字的笔划比俗字少的,仍然用本字,那么枪干的干似乎也该加木旁。这里“三干主义”,也不加竹头,也不加木旁,算是都简化了的。其实这个干字,如果当作幹的简化字看,所谓三干主义,就是拿笔竿的事情也干,拿枪杆和拿锄头杆的事情也都干,也是说得过去的。我们在永安足足八年半,的确是这样做了的。
前面我说了我在由福建师范到永安师范足足九年半,对于鲁迅先生也是不无关系的话。我上乌石山时,距鲁迅先生逝世不过一周年,我老是暗自戚然。觉得已经失了依恃,如果再被关进监狱,会有谁营救我呢?我选些鲁迅先生的作品做语文课的讲义,也讲些国语文法和图解的方法,这是鲁迅先生有意要我这样做的。还在福州时,为着搞抗日救亡运动,我和董秋芳、姜校长、郁达夫都上了黑名单。到了大湖不久,我就感觉到,校内颇有些穿蓝衣衫的人,竟有人在周会上大声说:“鲁迅不是好人,他写的阿Q,是不知道报仇的!”当是,我们的许多同胞,是无辜的,都被日本军阀杀害了,要提倡报仇是对的。但鲁迅先生正因为阿Q之流不知道报仇,才用反语讽刺的笔调写《阿Q正传》来提醒大家进行报仇的。他在薄薄的散文诗集《野草》上,标题《复仇》的,就有两篇。我国人民对帝国主义者的压迫,早就是受够的了,所以鲁迅先生生前,已经多方地提倡报仇。蓝衫者如此狂妄,真地看不懂《阿Q正传》,还是别有用心的呢?我是经常被指作“名字上打着记号的”,是警告,也是威胁。环境复杂,斗争激烈,同学们在文娱晚会上表现“锄头下面自由”的歌舞,似乎也成了问题。进步的同学三五结伴想悄悄地到延安去,未离县境,就被拉了回来。这种种,就是我前面写到“相处乐欢然”,要在后面的三个字上加个引号的原因。有些人,并无一定的事情联系,却故意来找我闲谈的,我总就以“今天天气——哈哈哈”的方式与之周旋。后来董秋芳编《燕江日报》的副刊,我校稿,被校外的一个文化特务同案控告,董秋芳坐了半年牢监,我严重地恐怖了半年。虎口余生,我即将83足岁。回顾当年,国难当头,我更有严重的家难。连集美中学和协和大学,我在福建先后任教11年多,福建是我的第二个故乡,也是我的避难所。蓝衫者究竟是少数,我对福建是有热烈感情的。妻也即将70岁,她是很快学会了永安话的,有人来大湖游十八洞等名胜,向她问路。听了她回答的话,说她是个会说普通话的“安答帝”(本地人)。她也常想再到大湖去看望要好的老邻居。庚儿已于1956年北京大学毕业,教了23年数理化。云儿在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,分配到云南华坪县办学,不幸于1971年患脑溢血死去。他吃过不少大湖的糕点,总算也在大西南的边疆上贡献了点力量。离开永安时还只半周岁的小女儿,1970年浙江大学电机系毕业,在北京服务即将满10年,已有两个女儿,小的也已8岁。这次我到北京去开会,回来时车经天安门,她用北京腔叫了我声外公,向南指着说:“这是毛主席纪念堂,这是人民英雄纪念碑!”活泼可爱。后一辈的儿童生长在幸福的新社会,这是可以告慰的。1961年我从南昌到井冈山而红都瑞金,瞻仰革命圣地,由长汀回来,道经永安,时已夜半,只见高楼林立,并闻工人人口已占全县人口的60%,塔旁大溪上的浮桥已经改建为固定的大桥,足见我的第二故乡已有很大进步。又听说,近几年来,永安已建成福建省重要的工业基地,煤炭、化纤、电力、汽车制造业等已名列全省第一,我受到了很大的振奋。永安必将在完成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中起巨大的作用。我是多么想念那高高的南北塔,如练的燕江啊,怀念那养育我的土地和人民。只是我眼病严重,行动不便,而且又有赶写纪念鲁迅先生回忆录的任务。因此,友好相嘱,难免延搁,或且终于无以应命,尚祈曲谅!自然,我是希望日后有机会,右目也动手术,多恢复些视力,以便再写些稿子。
1979年冬于杭州
(作者:许钦文,浙江杭州人,1936年8月至1948年2月在母校任教,文章来源:《闽师之源》,出版时间: 1993年7月